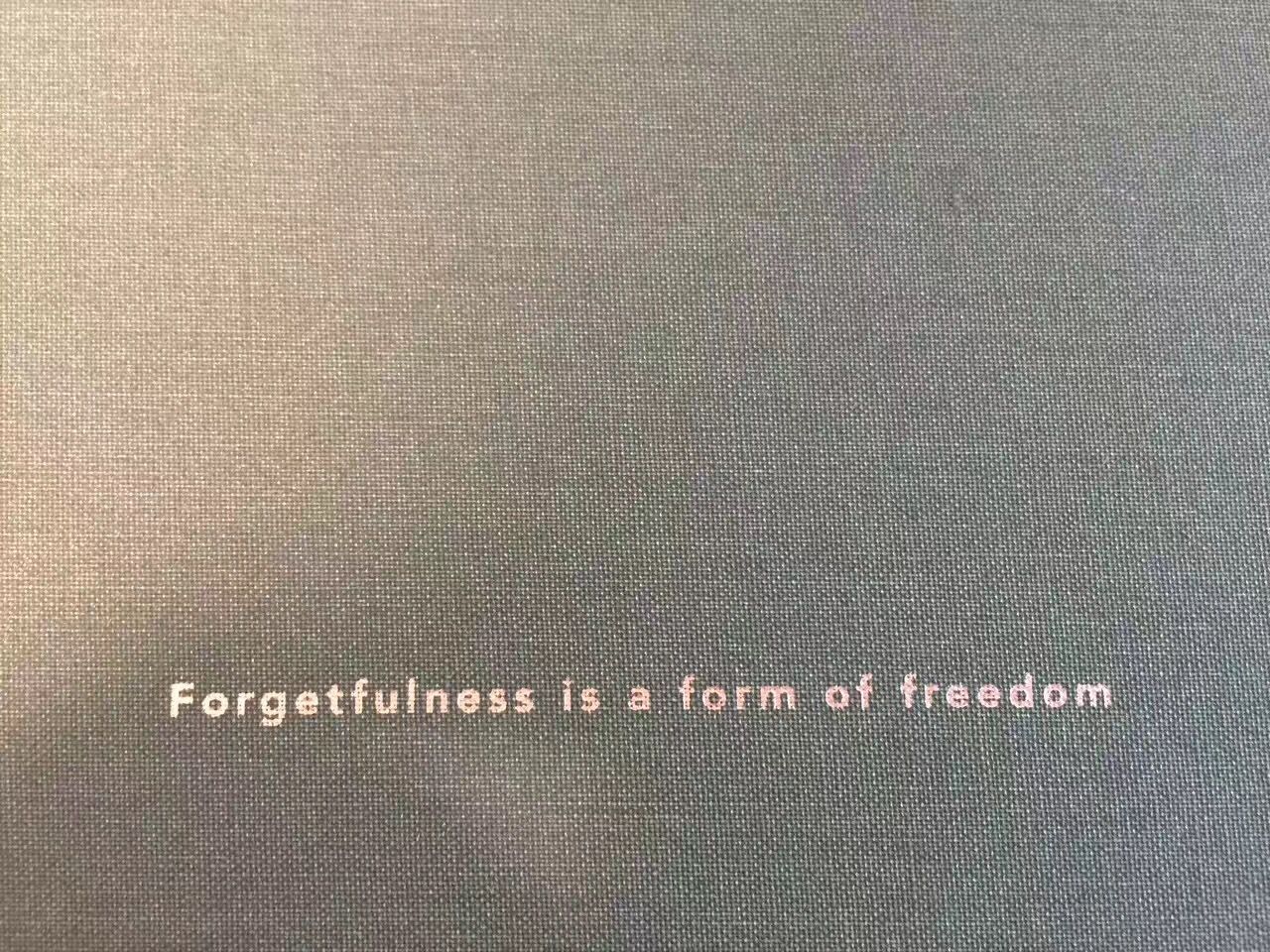八月。
打完这两个字之后我便不知道再写什么了,然而我还是写下了“打完这两个字之后我便不知道再写什么了”这样一句话。有时候无话可说,并非真的无话可说。当我意识到自己的沉默时,我便能够针对自己的沉默写下了一些评论,真正的沉默,要求人不对沉默本身产生任何意识,使沉默好似空气一样弥漫在空中,好似水之于鱼一样——你能每时每刻都意识到自己呼吸的空气吗?呼……吸……呼……吸,留意每一次空气的流动,竖起每一根寒毛,在每一次秒针转动之间都专注于——空气。倘若真是如此,人便无法正常呼吸,健康是器官的无意识,对沉默产生意识后,我便再也无法保持沉默。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对沉默产生意识的“我”是谁?难道此前沉默的不是“我”吗?在这似乎是“我-a”对“我-b”产生了意识,“我-a”认出了“我-b”,将a与b分开的那道深渊,则是时间。“我对沉默产生了意识”,有两步可能的情况,第一步,我感受到了时间,对时间产生意识,使现在的“我a”能够辨认出“我b”。第二步,我把b称作沉默,将其作为“我”的一种状态,好像“我-快乐”,“我-痛”,“我-悲伤”一样,在这里是:“我-沉默。”沉默与我仿佛装配零件一样,可组装亦可拆分,沉默是一颗螺丝钉,独立于我之存在。“我对沉默产生了意识”,即我对沉默这一存在产生了意识,产生意识的条件是:时间。到底是我离开沉默后,于是对沉默产生了意识?还是我对沉默产生意识后,我才离开了沉默?将对象换作时间来看,因为只有时间才能让我对时间产生意识,所以若要意识到时间,我便无法脱离时间,但我确实能感受到时间之存在。如果沉默和时间相同,那也就意味着我不必离开沉默再对沉默产生意识,或者是我离开x后再意识到x。然而这个命题的假设,即时间和沉默相同,很难站稳脚跟;时间将是个更加棘手的问题,我只能先将其搁置在一边。由该假设延伸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假设我能在沉默在场时意识到沉默,那么在那之后我能选择继续沉默而非离开吗?
“对于不能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如何理解维特根斯坦在这里的沉默?“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是一种来自于无能的沉默。要我对不可言说之物说些什么,对不起,我无能为力,就好像命令我搬起一块永远无法被搬动的石头。我们被迫沉默,在维特根斯坦这里,不是我们语言能力尚未达到,问题不是让刚出生的婴儿去描述《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无能,而是语言无奈的沉默,是语言的无能为力,是语言的界限,谈论的界限。
存在一种有意识的沉默,这是有意而为之的沉默,不开口,不写字,不做任何手势,目的是不传递任何信息,不做任何反馈。当有人跟我兴高采烈地谈论一部庸俗的烂剧时,选择面无表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做任何评论,选择做一根安静的木头,做一个活死人,我们将这样的行为称之为沉默。
维特根斯坦的沉默,是一种无能。而刻意为之的沉默,则是一种潜能。潜能不是我能做什么(I can),亦非我未来能做什么(I can do it in the future)或者我可能做什么(I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do),而是我能不做什么。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一种普通的潜能和一种弹性的潜能。前者指一个儿童有成为建筑师或国家领导人的潜能,后者则指建筑师有建造的潜能,歌唱家有歌唱的潜能。根据阿甘本对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建筑师有潜能,在于它可以不建造;乐师也是这样,因为与一种仅仅是普通意义的潜能不同,即与不会弹奏西塔拉琴的人相比,乐师可以不弹西塔拉琴。”在这里,有意识的沉默与潜能有着密切的关系。潜能意味着持有某中丧失(sterēsis),那么沉默就是持有丧失表达或反馈的能力,我能不说话,我能不发表评论,我能毫无表情,我能漠不关心。潜能就是有意识沉默所拥有的一种能力。更进一步讲,当我称自己有某种潜能时,我便是对潜能目标保持沉默。
然而不说话,无话可说,都只是表面上的沉默,一种传播学意义上的沉默,它尽管默不作声,却依然属于一类沟通方式,一项技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叫“沉默是金”。尽管我不掷一词,却依然通过“沉默”这种方式传递出了什么,比如:我的态度,沉默仍然是语境中的一角。沉默在此作为一种舞蹈——一种纯粹的展示行为——而进行沟通,其实背离了沉默之本意。
即使是那种将沉默转为其他行为的沉默,也并非沉默。比如王小波在对付一辆停在自己门口的自行车时,就打算采取沉默的对策:“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的厌恶之情:把他车胎里的气放掉。干这件事时,当然要注意别被车主看见。”王小波的意思是,在这场对峙中,我不打算使用语言,而将战术调整为直接的物理行为。在此,沉默的只有语言,行为主体并未真正沉默。再比如,拜占庭13、14世纪的伊思暇运动,提倡静默冥思。他们断言,长年离群索居,沉默不语,孤独入定,必将达到通神境界,乃至凭借修炼成果,即某种感觉-超感觉,便可以看见类似萨博尔山的灵光。沉默在伊思暇中便作为一种沟通手段,目的在于与神进行沟通,和发短信、打电话、大声呼喊无本质区别。
所以在这里便要问了,什么才能称作真正的沉默?
是否存在沉默的沉默?沉默的沉默是有可能的吗?于是,无意识的沉默出现了:意识的沉默。即使我正在打字,正在说话,沉默也是可能的,在此时,此处,我对自己正在使用的语言——或许“使用”这个词并不恰当,但姑且这么用——无意识,我全然相信着语言,任由语言寄宿,支配自己,否则我便无话可说。而这正是一种沉默,正因为我对语言保持沉默,从而开始说话;我对呼吸保持沉默,从而正常呼吸;我对“沉默”保持沉默,即在一个无稽之人面前不做声,不做响,以“沉默”的力量回击,此时我在“沉默”中沉默,我将自己全盘托出交付给了所谓的“沉默”。
在沉默中,我处于一种深度睡眠的状态,几近昏迷,直到我清醒过来,脱离沉默的深渊,我才开始思考。哲学的任务,思考的任务,便是和沉默作对,醒一次不够,要不断地醒,不断地醒。并非是要战胜沉默,不是像柏拉图的寓言一样,走出洞穴,彻底醒来,拥抱光明。不是这样的。哲学思考不是寻求彻底的清醒,而是一场不求胜利的拳击。思考仅仅是为了保持竞技的状态,倘若没有对手,拳头只能挥向空气。我们永远无法将沉默打倒,却要和它一直打下去,因为这就是生命之源,它让我们动起来,活下去。它是荒诞的,但也是现实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将沉默打倒,高喊十声它依然倒地不起,那便是我们输了,因为从此之后,没有对手的哲学家将陷入沉默。
回到最初的一个问题:如果我能在沉默在场时意识到沉默,那么在那之后我能选择继续沉默而非离开吗?答案是否定的,假如我们接受沉默即无意识的假设的话。当我意识到自己在讲笑话时,我就再也无法真诚地笑;当我意识到沉默时,我便无法继续留在沉默之中。在意识之中,总是存在着一种无能。意识为我们打开了新的面向,每一次新生都不得不为之作出牺牲。然而,在无意识中,在沉默中,人却是万能的。
可是,我们尚未提到,将要提到,明明还有一种沉默,明明还存在一种更彻底的沉默,那就是死亡。生者对死亡保持沉默,因为他们无法为死者说出任何有意义的建议或是问候,一切关于死亡的言谈都是为生者服务;死者同样对死亡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再也开不了口,不可能爬出墓地,爬出火化炉和生者打声招呼。生者和死者,都诉说着维特根斯坦的沉默。人类的死亡,动物的死亡,植物的死亡,甚至是粒子的死亡……死,并非是由谁发起的动作,亦非谁的无意识或漠不关心,它可能是最纯粹的沉默。实际上大部分死亡都死得不太干净,都只是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诸如泥土、大气、文字等,继续留存于世。在此,死仍然是生的一部分。只有一种绝对的死,没有任何转化等可能,它是彻底的消失,是涅槃,是死亡的死亡,是终点的终点,也是起点的起点。只有绝对的死,才配得上最纯粹的沉默。
最后看来,在沉默之中没有第三条路,鲁迅那句话大概就是对沉默,也是对人最后的审判:“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