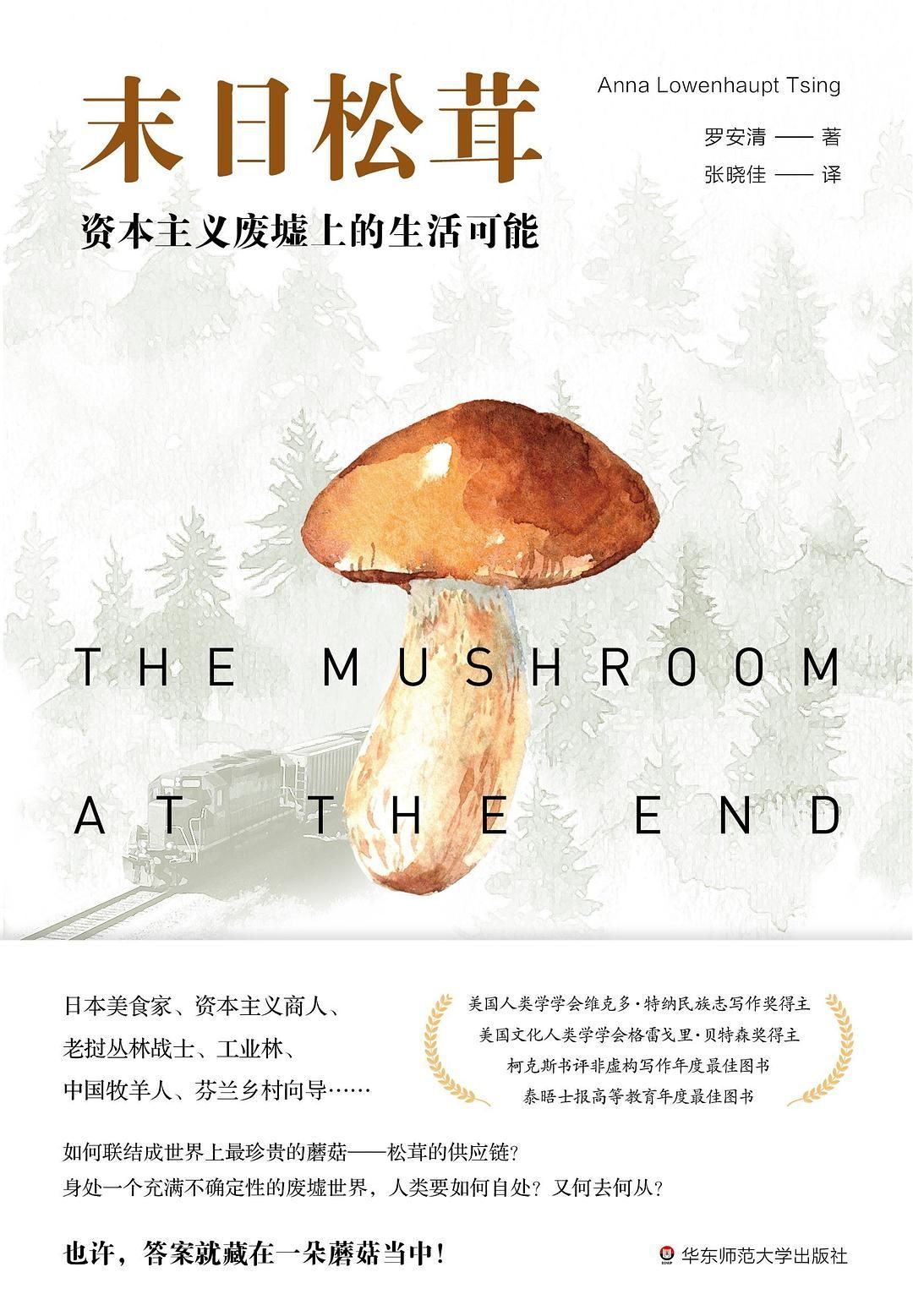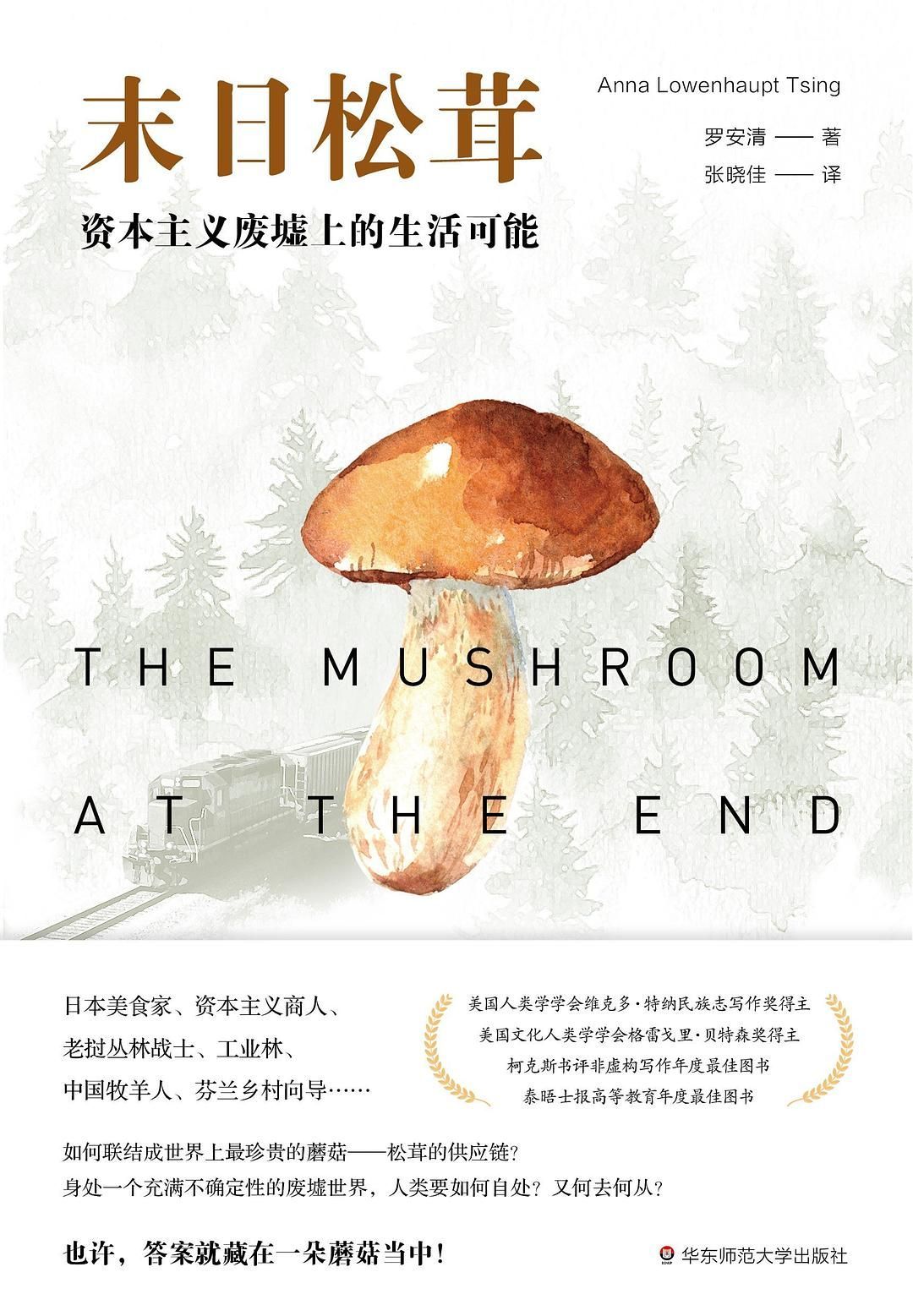先要明确的是,本书在一个大背景下展开探索:进步主义的幻灭。首先,共产主义式的乌托邦幻灭了,资本主义当道。然而资本主义也有其问题,尽管当下资本主义让世界财富积累越来越多,但是这个世界并非变得越来越好了,财富的增长只是表象,真相是世界财富前所未有的集中。资本主义的财富,是通过不断剥削劳动力产生剩余价值来积累的。简单说,就是富的更富,穷的更穷。你所赚的钱都是维持你继续被剥削的资本,打工人是也。
于是,在这个进步主义幻灭的后现代背景下,有一群逃避打工的人(在此作一个限定:美国。因为云南的采摘者动机很不一样),他们不甘过领工资的生活,捡起了松茸。
首先我们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松茸?
显而易见:
1. 松茸至今不可培育,只能野外摘;(稀缺)
但是云南有很多野生菌不可培育,并且都价值不菲,比如干巴菌,为什么不是其他野生菌?
所以还有其他前提条件:
2. 日本人喜欢松茸(有买方)
3. 日本太小,资源匮乏,松茸供应跟不上,于是要去海外进口松茸(找卖方)
由此一来,一个国际市场就这么形成了。这里必须强调国际性。而产业链的国际性则意味着这门生意的产业链很长,长到需要有许多中间方参与“转译”。这中间松茸就必然要被异化成为商品,被贴上标签以被计算,一朵朵野生菌要变为excel表里的统计数据,变为库存,变为资产。云南也有很多其他珍贵的野生菌及买方,但始终只局限于云南,形成不了一个长长的资本链条。因此,日本作为海外的买方这个身份尤其重要,使得松茸成为本书论述资本主义问题的最好对象。
然后我们问第二个问题:人们为何去采松茸?
这个问题没有单一解释,作者试图去观察并归纳总结,寻找答案。罗安清通过对俄勒冈州的人类学调查,发现俄勒冈州的采摘者中,亚裔是曾经逃至美国这个“乌托邦”的“战后难民”,包括“战二代”,有“流亡者”的特质,他们向往曾经美国梦式的“自由”,来到美国。
他们选择采摘的动机很复杂,有的日裔是因为怀乡;有的东南亚二代移民,因为美国福利紧缩而无法顺利分到美国社会的蛋糕,而进入森林选择这样的谋生手段;有的则是喜欢这种丛林式的生活方式。
采摘者中也有白人,这些白人大多是喜好野外狩猎的白人,也有老兵,他们不愿过领工资的生活,森林是个更好的选择。
也有大部分人是为了追逐利益,但这种逐利的方式有种西部淘金式的自由感,是一场冒险,这也是松茸采摘的迷人之处。
总而言之,这帮人有个共同点,就是很“野”,都不是社畜。而罗安清所探讨的就是他们“何以不成为社畜”,我们有没可能在人人皆社畜的时代不成为社畜,以及怎么能一边不做社畜一边又参与到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当中。
—
罗安清首先打破了我们对采蘑菇的嬉皮幻想,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以为采个蘑菇就逃出资本主义了?No,请深刻地意识到,当今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二十世纪。
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PK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化解资本主义的问题的方法,不是要建立另一个乌托邦去对抗它,或者找个地方逃出去。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你无处可逃,所以你只能想办法在里面活得痛快。即使是采蘑菇的人,也是活在资本主义链条里的。她把采摘松茸称之为一种“谋生区块”,
每一种谋生区块都有自己的历史和动态……没有哪个区块是具有‘代表性的’,因此也没有哪个团体斗争可以单独颠覆资本主义。P159
从经典资本主义模型(工厂流水线)中漏出来的美国采摘者们,为了怀乡或自由,无论什么浅层的深层的原因,不约而同地采起松茸。然而松茸在经过海外“保值票市场”买卖后,装箱上船,再次被分为各个品级,贴上标签,成为超市库存的一员,最后也会变成资产重新回到资本链条当中,成为被异化的商品。
所以,在松茸采摘这一环,即使你是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你其实也参与到了资本主义的链条当中。
罗安清的人类学研究,就是向你展示了这样一幅政治经济的生态图景,这个结构中的每个单元都缠绕在一起,它是一种动力学。
一切都没逃过资本主义的法网,这听起来绝望吗?倒也不是,罗安清想要寻找的就是采蘑菇这样一种生活可能。本书没有要颠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计划,但通过罗安清的田野调查后,使这种资本主义内的非资本主义生活可能呈现了出来。采摘者们在资本主义内部寻找这种“被允许的自由”,他们就是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
工业成果不再是未来的蓝图。生计是多种多样的、东拼西凑的,而且往往也是暂时性的。大家基于不同的原因工作,但很少是因为工作还能像20世纪那样给予梦想中稳定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开始观察谋生区块如何凝聚成一种集合体。其中的参与者各有不同的日常生活,在世界创造计划里扮演着一个小角色……这些计划动员了商业采摘,吸引了大批采摘者进入森林去追逐“蘑菇热”。尽管这些计划存在着差异,但边界目标已经形成——尤其是对采摘者所谓的“自由”的承诺。通过这种想象的共同基础,商业采摘成为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场景——而且聚集成一场正在发生的事件。通过它新兴的特质,多向度的历史成为可能。若没有自上而下的纪律或者同步性,没有对进步的期望,区块谋生方法将有助于建构起全球政治经济。p157
而这种生活可能之所以可能,一个前提条件,便是松茸这种无法被驯服的存在。这在本书的后半部分被称之为“潜在公有地”(latent commons),它是森林,是自然,是生态,但它们并不是那种遗世独立的存在,而是人“为共同的原因动员起来的缠绕”,由此将成为一个像松茸一样的谋生区块的可能。
“潜在公有地”,看上去很香,罗安清给了我们希望,但她也给了我们警告:
1.潜在公有地不是人类独有的领地。向其他生命开放公有地可以改变一切。一旦我们接纳了害虫和疾病,我们就不能指望和谐;狮子无法和羊羔和平共处。而有机体不只会吞噬对方,也会制造不同的生态环境。潜在公有地就是在这种混乱的交互作用下,由那些互助共生的、与非敌对的缠绕关系所构成。
2.潜在公有地并非能使人人受益。每一起合作案例都只能为特定对象腾出空间,继而放弃其他;有整个物种在合作中被淘汰出局。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争取“足够好”的世界。而“足够好”意味着总是不完美,并且始终在修正。
3.潜在公有地不能被充分制度化。尝试将公有地转化为政策的勇气值得称颂,但并未捕捉到潜在公有地令人雀跃的本质。潜在公有地在法律空隙中移动;它是由违规、交染、不经意和盗猎催化而成的。
4.潜在公有地不能拯救我们。一些激进思想家希望“进步”能引领我们走向救赎人类和乌托邦式的公有地。相比之下,潜在的公有地是夹在麻烦之中的此地此刻。人类无法完全掌控。P314
潜在公有地不是一种承诺,我们不要以为它能带给我们美好的明天。这又回到了她的人类学视角背景:进步主义的幻灭,随之而来的是没有被许诺的乌托邦,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我们就是要面临这种不确定性,这是我们对生态复杂性的后现代观察得出的结论。
那么,没有进步,我们生活是为了什么?没有点盼头,教人怎么活?我们斗争的理由是什么?寻找潜在公有地的理由又是什么?在罗安清对松茸采摘者的调查中,我们得到了一种看似很美国式的启示:今天我们不为进步,我们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