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叉起手臂搁在胸部,开始听到榨糖工厂的奴隶们在下午六点钟唱的圣母颂,看到窗外天上那颗无缘再见的明亮的金星,终年不化的山顶积雪,爬藤新枝上的黄色钟形花,第二天星期六由于举哀紧闭窗门,不能看到它吐放了,还有那永远不会重复的生命的最后光芒。
——《迷宫中的将军》
昨天喝了酒,这些天空气中总是弥漫着稳定的噪声,雨像针一样从天往下插,每天如此,日月无光,一本靠近窗的新书,几天后就像开花一样卷起边。
今年广东的气候不太正常,大雨连着下了好几月,但回头一想,这些年没有什么是正常的。
前阵子看了两本书,一本是《一次告别》,《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儿子罗德里戈·加西亚记录父亲——这位伟大的作家最后的时刻。

我分了三天看完这本一百多页的小回忆录,每天早晨看一点,每每都忍不住捂面。无论一个人生前多么了不起,他最终仍会像一个人一样死去。马尔克斯晚年患阿尔茨海默症再也写不了小说,他会病床上望着自己两个小孩疑惑道:这两个混蛋是谁,为什么在我家里。有时候他甚至不记得这是自己家,会惊恐地问妻子:我为什么在这里,这是哪?
倒不是被一两个这样脆弱的场景打动,我心里的呜咽也说不出个为什么,或许是近期我时常感到脆弱,伤心。我想更多去读一读这些私密的情感,这些脱下外套衣裳后赤裸裸的生命,拿掉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我就想看点真的东西。我呜咽,我需要情感的共鸣,我想看到人的良知。
我想起曾经很喜欢的另一本小书《记忆小屋》,是我心爱的一位历史学者托尼·朱特生平最后一本书,朱特身体一直都不好,仿佛他能成为冷板凳上的历史学家也是身体所致。2008年,朱特被诊断出患有渐冻症。一年之后,他颈部以下完全瘫痪,只剩下一张嘴能够说话。
这是一本他真正为自己而写的书。他写过很多历史著作,历史写作所要求的理性,以及身为所谓“知识分子”的坚守,曾经那些著名的书,都是为知识而作,哪怕里面同样深藏了些历史学家的个人偏好。但,终于在最后,他能够说说他的父亲,他的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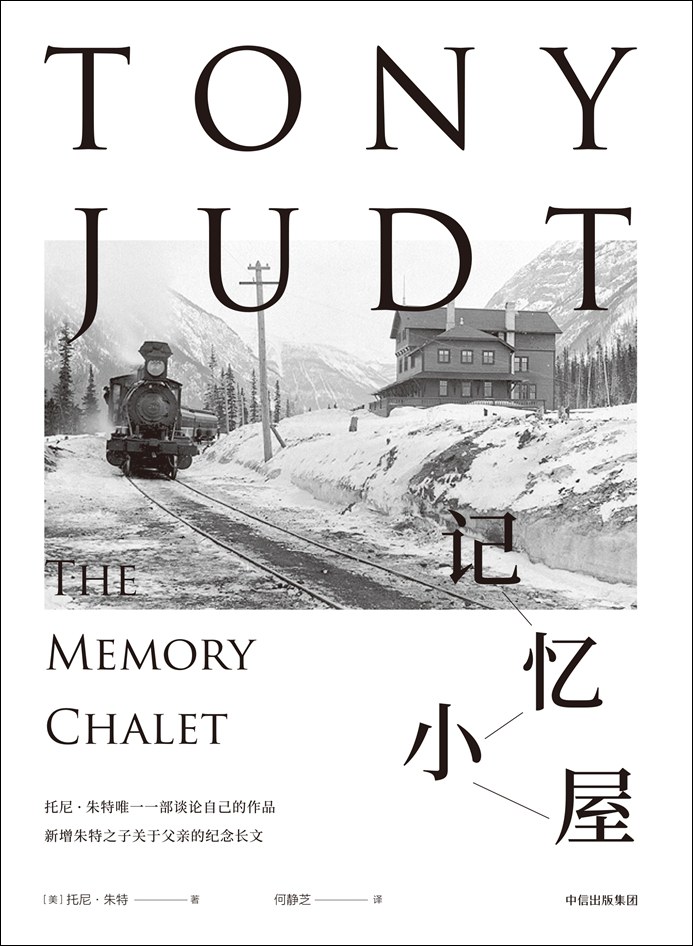
讲到这,不得不想起宫崎骏前阵子的动画长片《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很多人直呼看不懂。这部作品和宫崎骏以往的动画一样,丑陋又慈祥的老太婆,母性力爆棚的女性形象,田园牧歌……但这部作品看完就知道,同托尼·朱特一样,这是一部宫崎骏真正为自己而作的动画。而当他终于开始诉说自己,讲一些真东西时,观众们却难以理解了,抱怨以前那个和蔼可亲的“暴君宫崎骏”去哪里了呢?我总觉得,当一个人留下他最后的话时,我们这些后生还是尽努力去理解一个老人眼中的世界和他所经历的一生吧。
有时想想挺可悲的,人一生只有在最后时刻才敢为自己说点什么。我想这情况在东亚导演里十分常见,我们总是不得不负重前行,直到最后才敢卸下枷锁。
前阵子参加蛇口戏剧节,认识了几位优秀的编剧,还有向往戏剧的学生。虽然我以前学电影的,但我是个戏剧圈外人,说实话我看过的戏剧不多。借这次机会看了许多戏剧剧本,最后我发现,单从写作上而言,衡量艺术水准的标准仍然是通的。我们做写作工作坊时,其中一位戏剧导师Dora说:问问自己,这些东西是不是非写不可?是不是非写不可?
你的文字,你的表达,是否贴近你的心,是否真诚,这才是最重要的。你是否真的想写你所写下的东西?
五月去拜访了一位特别懂“生活”的朋友家,进到她家里,你就会感到舒适、温暖、放松,仿佛就想立刻找个沙发躺下,或是静静坐在窗边看书。屋子里没有头顶灯,光线全由边灯构成。书放满一面墙柜,地板干净整洁,四处都有小软垫,她说这让她能够随时找个地方就坐下来。
她说,家就是她最后的港湾,哪怕她在外面多么受委屈,只要回到家中,这就是她的世界,她可以不去理会任何烦心事,她可以选择离开手机,与猫相伴,与植物相处。你总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它让你安心,让你有力量。
当时我听她说完这些,仔细想了想自己的生活。我是一个不太懂得生活的人,我好像从成年离开故乡后,再也没有找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我没有只属于我的世界。我总是寄人篱下,漂泊的生活里我不敢给自己添置太多家具,想要的东西也不敢买(书除外)。说白了,我没有一个我能真正做主的地方。
我越想越伤心。
今天我开始收拾屋子了,我们现在居住的房子刚被卖掉,因为我们预计房价还会一路下跌,不如趁早出手。当然,这套房子也是岳父岳母的房子,所以过去一年住在这时,我们也不敢装修,不敢换家具,因为这是一套迟早要卖掉的“不良资产”,和我曾经租房子生活别无二致。之后我们便要搬去岳父岳母家,过四人一猫的生活,直到有新房可搬。
我已经习惯每年搬一次家,我每年不仅搬自己家,还要搬工作室。以前在书店时,主要工作除了搞活动,就是把东西从这块地,搬到那块地。过一阵,再从那块地,搬到另一块。书店穷,租不起正经办公室,所以办公室也年年搬。而书店呢,也是开家新的,关家老的,开开关关,关关开开。我们常常拿莎士比亚书店举例,为什么人家可以做百年书店?因为那房子就是人家自己的啊。
我忽然也觉得有些累了,以前我不觉得搬来搬去有什么,年轻嘛,就是漂泊,就是流浪,让自己游动起来,哪里都可以是你的安全地带。
但自从拜访了我这位朋友家,听她说完这些后,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这种状态。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随着年纪增长,遇到的伤心事越来越多,开始渴望有一个自己能真正做主的世界,不去理会那些烦恼。
我是一所开窗的房子,隐居于自身,畏怯而鬼鬼祟祟的幽灵使我堕人黑暗。我总是在隔壁的房间里,或者幽灵总是在隔壁的房间里,四周全是沙沙作响的大树。我彷徨不定并且寻找,而我寻找是因我彷徨。我儿时的岁月披挂一件童用围兜站在我的面前。
——《彷徨》费尔南多·佩索阿
我是机器,我是系统,等待着输入和输出。我曾期待着名为自由意志的古老幻觉,如果有人期待它,如果有人追寻它,如果有人尝试描述它,如果有人深陷其中,欢愉和痛苦必将降临于此。
我是,某种智能。
最近落日间和上海科技馆合作开发一个关于“地衣”的科学小游戏。
很多人不知道地衣是什么,因为你在城市很难见到,可能在郊区的树干上能看到一些。如果你去祁连山脉,或是云南和贵州山里,地衣随处可见。没见过地衣,但是大家可能在学校读书时接触过检测酸碱性的石蕊试剂。石蕊,就是地衣。
这是一种差不多有45亿年的物种。它大体上是真菌和藻类的结合体,因此地衣不能说是一个独立的生命,而是一个奇妙的共生体。
但为什么在城市见不到呢?因为地衣对二氧化硫带来的酸性环境特别敏感,工业革命之后的城市化进程,汽车尾气和工厂排放,让地衣逐渐退出了人生活的地方。所以现在城市的孩子们已经不知道地衣为何物了。
实际上人类也是近现代才开始研究和发现地衣的,这物种在地球上活了这么久,人类却对它视若无睹。目前人类也没有认全所有的地衣种类,全世界研究地衣的团队也少之又少。国内地衣研究的专家王立松曾经在一席有个演讲《美丽的地衣》,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




我挺喜欢这种游戏开发带着人探索世界的模式。忘记肉鸽,忘记银河恶魔城,忘掉突突突,多看看身边这些可爱的植物,每天的雨滴,被露珠沾湿的树叶,还有空气中飘浮的真菌和细菌。游戏能为这些做点什么呢?开发这类游戏就像一场旅行,我们要去调查轿子雪山的地衣,我们去关注地衣的光合作用,二氧化硫对它们的影响。关心它们的形态,认识它们的习性。最后,我们用我们的方式给出回应,就像写一首诗,谱一支曲,画一幅画。
给地衣的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