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我的第一个画面,是1965年在冰岛一条路上的三个小孩……他写道:’我会将它单独放在影片开头,和很长一段的黑画面一起。如果他们没能从影片看到快乐,至少他们能看见黑暗。’”
熟悉克里斯·马克的影迷,一定忘不了上面这段《日月无光》(Sunless, 1983)的开场白。它值得你仔细听上百遍,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几乎能够以克里斯·马克命名的电影类型——信件电影(Letter Film)。
关于信件电影的研究并非很多,最早出现信件电影的研究应该是Hamid Naficy的著作《带口音的电影:流亡与流散的电影制作》(An Accented Cinema: Exilic and Diasporic Filmmaking), 在其中他第一次使用了“信件电影”这个术语,而代表对象就是马克。
但什么是信件电影?是那种以电影的形式写一封信的电影吗?我们能用电影写信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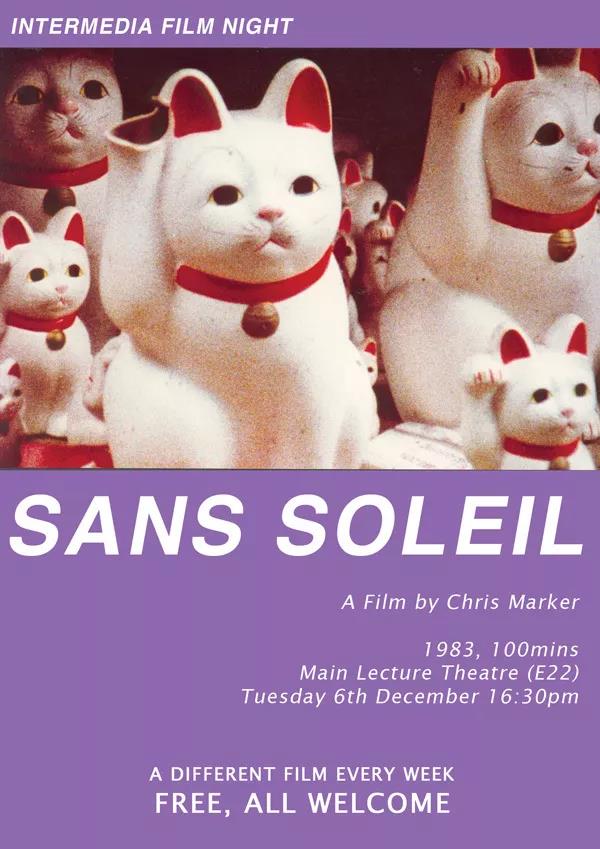
信件式的论文电影
早在1957年,克里斯·马克就在他的异域纪录片中融合了自己写信的才能,拍出了一部早期影片《西伯利亚的来信》(Letter from Siberia, 1957)。这部电影的第一句台词是:“我从一个遥远之地给你写信,它的名字叫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当时对于法国来讲像是一块蛮荒之地——苏维埃政权到底在搞什么呢?该影片是马克到西伯利亚旅行,拍回了一部当时被人们称为“论文电影”的纪录片,而马克用写信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
观众(们),我的观众,这封信不是寄给别人,正是寄给你(们)的。信是一种极具勾引力的文本形式,它像是一个礼物,一个突然而来的惊喜。克里斯马克的传记作者Catherine Lupton评论起《西伯利亚的来信》时说道:“这种亲密的(intimate),勾引性(seductive)的个人信件写法能够直接把观众拉入情境之中。”

信件上通常会有署名,来自谁,寄给谁。假如收信人提到我的名字,我便会竖起耳朵来听,因为有人要通过信告诉我一些藏在信封里的秘密。不过用电影写信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这手法并非马克一人所有。戈达尔也乐于使用这种方式来向观众们布道。1972年,戈达尔和戈兰拍了部短片叫《给简的信》(Letter to Jane, 1972)。简(Jane Fonda)是戈达尔同年影片《一切安好》(Tout va bien, 1972)的女演员。《给简的信》开头第一句也用了信件的通用格式称呼收信人:“Dear Jane…”

这部影片像是一封写给简的信,但更像一封放给所有观众看的演讲稿,只不过被包装成了私人信件。和马克的柔情和幽默不同,戈达尔和戈兰全片仅仅通过一张简和越南士兵的照片狠狠地表达了他们的政治批判。这部电影信不在乎任何回应,几乎以法西斯式的演讲完成了这部52分钟的影片,这也是戈达尔和戈兰的最后一次合作。
另外一部2015年的越南电影《来自宾童龙的信》(Letters from Panduranga, Nguyen Trinh Thi, 2015),算是继承了早期马克的风格,电影第一句台词就直接模仿了《西伯利亚的来信》:“我从一个看起来像是遥远之地的地方给你写信,它叫宾童龙。”

越南政府计划在占婆族的圣地宁顺建造两座核电站,这计划两千多年的文化命脉造成威胁。导演则通过动态肖像的凝视,还有马克式的音轨评论,试图去从当下的影像中挖出更久远的历史母系——历史都写在了每个人的脸庞上。如果说马克摄影机下的西伯利亚连接起了他的观众和关于“蛮荒之地”的想象,那《来自宾童龙的信》则是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是信件电影,而非信件式的论文电影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所有关于信件电影的讨论和想象,基本都还停留在马克《西伯利亚的来信》中所展现的形式。
从导演的角度来说,艺术家通常有旺盛的表达欲,而写信这种私人化的表达方式,正好满足了他们倾诉的欲望。Naficy因此说道:信件式的电影正是许多独立电影最爱使用的形式之一。
当然也因为用电影写一封信不需要什么成本。
从电影研究者的角度来说, 人们也很容易把信件电影和论文电影混为一谈——Naficy就是这么做的,他并未分清楚《西伯利亚的来信》和《日月无光》在信件形式上的差异。
马克从未放弃过他对信件电影的思考,从1957年到1983年,他的思想路径早已有过至关重要的变化。
当我们讨论信件电影时,首先我们要问:什么是信?信难道仅仅是以“敬爱的……”开头,以写信人落款署名的文本形式吗?如果是这样,信岂不是就只是沦为一种文本框架?为什么我们平时用即时通讯工具发送的微信和短信,我们只会叫它们消息(message),而不会把它们称之为信件(letter)?为什么同样是传达信息,有的叫做聊天,而有的叫做写信?
因此当我们在思考信时,我们不能纯粹从文本本身出发,还要考虑信的物质与时空属性 。一封信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写、寄、运送、收、回信,再如此循环。德里达在“The Post Card: From Socrates to Freud and Beyond”中提醒我们:信是在“抹除”中写作的。意思是当我们讨论信时,我们不能忘记信是如何被审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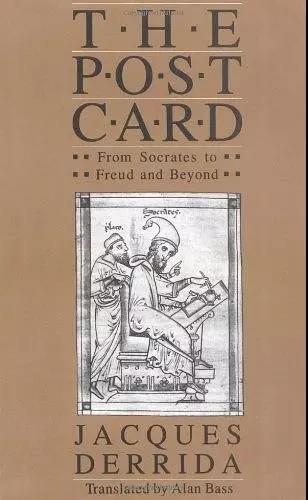
这些关于信件的实际操作告诉了我们关于信的几个重要元素:
1.必须要有写信的人;
2.必须要有收信的人,即使收信人是自己,即使最后信因为各种不可抗力无法交到收信人手中;
3.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写信与收信之间一定存在着较长的时间差。
这些各方面要素的集合才完成了信的流通,一封信才能被称之为信。
小时候老师都让学生写过一封叫做“给未来的自己”的信。学期前,你写好这封信,再交给老师统一保管。到学期末或者毕业时,老师再把你当初写的信交还给你,正是这种时差让这篇文本以信的方式真正生效了。假如你当即写完当即读它,你不会有任何感觉,只觉得那只是一堆字罢了。
因此一切对于信的感知都来自于后置,来自于时间的割裂。马克在《西伯利亚的来信》中很敏锐地把握到了信的精髓:“遥远”(distant)。只是这种遥远不一定是地理上的,更是时间维度上的。
信是一种时间的介质,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战争史会经常写到这样的故事:远在战场的丈夫利用夜晚的时间给妻子写家书。这封家书会先到邮局,交给邮差,邮差坐上火车,到达这位军人的故乡,交给在家的妻子。
有时候军队会等到大家都写完,再统一寄出,这中间可能经历一个多月乃至半年的时间。
有时候妻子收到的是好几封家书,包括丈夫战死的消息。倘若是这样,信所带来的时差感会更加强烈——妻子带着丈夫已死的事实,打开信封读丈夫生时写的战场琐事和对她的思念,然而每一行字都无时不刻在提醒着妻子,这些都已是回不去的往昔,令她更为痛苦不堪。
《日月无光》中也有一个相似的情节。在马克所展现的“禁区”Zone中,我们听到来自于日本神风特攻队飞行员上原良司的遗书:
“我一直认为日本人要自由,才能得到永生。今天说这些似乎有些愚蠢,但在极权的领导下,我们这些特攻队飞行员是机器,我们无话可说。除了向我们同胞乞求,希望他们能让日本成为我梦想中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在飞机上,我只是一具机器,只要穿上一点有磁力的盔甲,我们就会完全被吸附在飞机上。但在陆地上,我曾是一个有血有泪的人。请原谅我这个叛乱的想法,我带着非常悲伤的表情离开,但在内心深处,我是快乐的,因为我说出了真心话。原谅我……”
这封信伴随着那些令人心绪复杂的影像:日本神风特攻队员起飞前喝下最后一杯清酒,和亲人朋友告别,上飞机,最后在云霄处坠落,炸毁。它们被称之为Zone的技术电子化,呈现出一种迷幻的效果。这封遗书在当下,此刻,寄到了观众的耳道里,同时也第一次通过电影目睹这些过去的影像,不由得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撕裂感,和妻子收到战死丈夫的信如出一辙。

这些便是马克从1957年对1983年对信件这一形式思考的转变:如果我们要拍一部信件电影,我们并不是要用电影来写一封信,我们应该运用“时差”这个信的内核来拍电影。
回到《日月无光》的开场白,我们把它和《西伯利亚的来信》以及之前提到的其他信件式论文电影比较一下,会发现后者的视角通通站在写信人“我”这一边。这些电影中,收信人都是缺席的。而《日月无光》的开场白却以一个收信人的角度读信,内容来自于与收信人的转述——“他说”和“他写道”,强调的是“他”。读信人提醒观众:他拍摄的冰岛片段来自于1965年,即来自于过去。这种浓浓的距离感才真正体现出《日月无光》的信件属性,它是真正的信件电影。
另一部从收信人视角去讲述的电影是香特尔·阿克曼的《家乡的消息》(News from Home, 19777)。电影拍摄的是纽约城市的景观:布鲁克林区、地下铁、城市的街道、穿梭的人群……阿克曼在这些固定机位影像中念母亲的一封一封的来信:亲爱的女儿,你在餐馆工作的怎么样?听说你最近搬家了……听说你想拍一部电影,我们永远支持你……我们给你寄了些钱,你收到没……你一个多星期没有给我们写信了,要多写一些信……期待你的回复,我们都很想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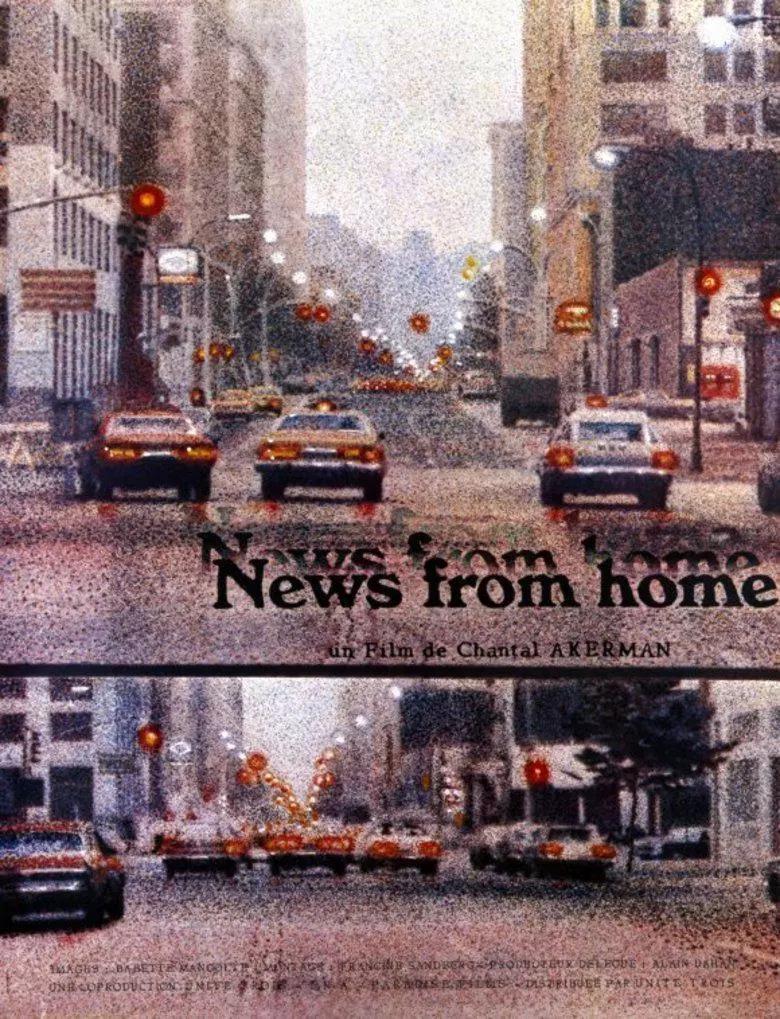
《家乡的消息》是一部纯粹的读信电影,我们借收信人之口,听写信人的声音。然而听到的永远是来自于过去的消息,信里的内容无不在提醒我们这一点——“上周……”上个月……”同时通过摄影机之眼看到阿克曼所看到的景象,彩色影像的现时性,随时把观众拉回她所在的当下,如此给观众制造一种时空的撕裂感。
《家乡的消息》算是信件电影的基本款,其中收信人的主体性并未主动体现,而是隐藏在阅读声中。在《日月无光》 中并非如此。电影里那充满忧郁的女声在转述旅行摄影师Sandor Krasna在世界各地发回来的信件和拍到的影像时,并非只是单纯地读信,从中她也夹杂着自己的评论。
此时她又变成了这部信件电影的主人,是一个积极的表达主体,仿佛她也在写一封信,一封主动的回信。收信人不是一开始那个“他”,而是在银幕前的观众,因此她在影片中拥有双重身份。通过这样一种简单的转变,写信、收信、回信,三个环节都在电影中得到体现。
尾声
信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它在写信和收信的时差中生效。然而这门艺术一直在消亡,如果我们观察人类的通信史,不难发现我们一直在通往即时通信的道路上蒙眼狂奔。
汽车、火车、飞机的发明,加速了送信的速度。后来出现了电话,出现了互联网,人们不再需要邮差,只需要服务器。到现在我们能够视频通话,开视频会议。信这种时差艺术将逐渐被人遗忘。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忘记马克,他不是写信的大师,但他在电影中重新发现了信的活力。电影的过去性——我们看到的将永远是过去拍摄的影像,以及现时性——我们无不在当下看电影,使电影这门艺术成为信的隐喻。
